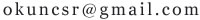小学五年级小品搞笑的 小学五年级四人搞笑小品 五分钟
www.zhiqu.org 时间: 2024-06-13
卖挂票
台词:
甲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,这个台词,跟其它的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。相声它这里头啊,它也有文言、也有成语、也有谚语、也有俗语、也有小市民语气,有地方语,那是很多。
乙 哎。
甲 戏剧就不是啦。话剧呢,它就不能说大白话,大部分是文言。京戏啊?那京剧,它就得呀,它单有京剧的台词。它就跟咱们普通话一样啦。
乙 是啊?
甲 哎。别忙——它就不能说“别忙!”“且慢!”——戏剧的“且慢!”。
乙 哎。别忙。
甲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,平常谁这么说?你刚走那儿—— “且慢”。可舞台里头懂——你听着戏,他说:“且慢!”听戏就是“别忙”,让他“打住”。“罢了!”是“得啦!”一见面,请安,“参见老大人”、“参见父母”、“参见爹爹”——“摆了”。咱平常不用,“老没见,你好啊?我给你请安!”“哎,得啦,得啦!”不能“罢了”!用不上。这舞台上它有舞台词——“罢了”!“且慢”,“呜呼呀”!“呜呼呀”是纳闷儿,“呜呼呀”!不信?“你待怎讲?——你再说一遍——你待怎讲?”
乙 哎。
甲 “嘟!”是急啦。“嗯?”是不乐意了,不乐意啦——“嗯?”“嘟!”急啦!这场戏见官儿,给官儿跪下,最好是:“呜呼呀!”这犯人准有好处,带上堂来——“给大人叩头!”“抬起头来!”“小人有罪不敢抬头。”“恕你无罪。”“谢大人!”官儿一瞧:“呜呼呀!”行啦。
乙 怎么?
甲 呜呼呀!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。详细审问,好啦。“嘟!”——坏啦!
乙 怎么?
甲 倒霉啦!“给大人叩头。”“抬起头来!”“有罪不敢抬头。”“恕你无罪!”“谢大人!”“嘟!”倒霉,准糟!
乙 生气了。
甲 那可不!这戏剧很深,下功夫最难。“唱、打、做、念、翻”,这个……这个舞台上……
乙 哦,您对京戏很有研究?
甲 研究干吗?你不认识我?你不常听戏。
乙 那你?
甲 你常听戏吗?京戏,你听不听吧?
乙 我从小就爱听戏。
甲 你要常听戏,你不能不认识我。你不能不认识我!你认识我吗?
乙 不认识啊?
甲 你看看!你细看看,哎呀……你们爱好京戏,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我。
乙 是啊?
甲 你怎么不认识我呢?
乙 您是哪一位?
甲 杨……
乙 杨?
甲 杨宝森!
乙 杨宝森?你是杨宝森?
甲 真是不认识,拿我……拿我当杨宝森。我不是!我不姓杨。谁杨宝森?拿我当杨宝森!我不是杨宝森哪。
乙 您是谁?
甲 提杨宝森这个人,你知道不知道?
乙 知道。
甲 我给他蹬三轮儿。这多少年了吧。
乙 多少年了?哎,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儿啊!
甲 那玩艺儿!
乙 那玩艺儿也是蹬三轮儿啊。
甲 他蹬三轮儿,蹬我。
乙 哦,蹬你!拿你当三轮儿啦?
甲 拿你当三轮啦!我坐……我坐那儿,蹬三轮儿那蹬着,后来我让他,“你蹬宝森吧!”宝森净闹病,车是我的,我送给宝森。
乙 啊,送给他了。
甲 我不姓杨。
乙 哦!您是?
甲 马!北京你打听打听!北京你打听打听,唱戏的马老板!那谁不知道啊?
乙 哦,北京马老板?马连良?
甲 马连良干吗?马连良是我们本家,我们都一家子。
乙 哦,一家子。
甲 马连良是“连”字儿的。
乙 对。
甲 “富连成”,他排字排“连”字的!我们科班儿,那时候叫“喜连成”,听说过吗?
乙 听说过。
甲 “喜连成”!哎,我们“喜”字,雷喜福?知道吧?
乙 雷喜福,大师兄?
甲 哎,对。
乙 知道。
甲 我们一块儿的。这还用说吗?侯喜瑞知道吗?
乙 知道哇。
甲 侯喜瑞——“喜”字嘛,陈喜星、康喜寿、魏喜奎……没有魏喜奎,魏喜奎她改大鼓啦。
乙 没改!一起就唱大鼓的。
甲 不是魏喜奎,什么“喜奎”我忘了。
乙 哎,刘喜奎。
甲 刘喜奎,对。反正我们都“喜”字儿的。
乙 哦,您叫?
甲 喜藻。
乙 洗……我修脚。
甲 修脚干吗?
乙 你洗澡干吗?你那儿洗完啦,我这儿……。
甲 喜!排“喜”字儿那个“喜”呀。
乙 那个“喜”呀?
甲 不是洗澡的那个“洗”。道喜、福禄寿喜的“喜”。
乙 噢!澡?
甲 藻是那个……这个字还说不上来。
乙 他连名字都说不上来。
甲 草字头那个……我想想草字头那个。
乙 李盛藻的那个“藻”。
甲 哎,你要是不提,我还把他给忘啦!李盛藻,听过吗?
乙 听过。
甲 唱的怎么样?
乙 好啊。
甲 别捧,别捧!别捧,别捧!说实在的,李盛藻唱得行吗?
乙 不错。
甲 你认为怎么样?
乙 都认为不错。
甲 服吗?
乙 服!
甲 那就完了,那咱就没杠抬了。你服,就完啦。那我就……行啦。
乙 我服李盛藻,碍着你什么啦?
甲 你要服李盛藻就行啦,
乙 怎么啦?
甲 你认为盛藻好,那就成!我痛快。
乙 与你何干?
甲 他跟我学的。
乙 李盛藻跟你学的?
甲 有人听过吧?李盛藻唱的怎么样?他完全学我,也就是我教戏。我当初在科班时候,我给他排戏,那都是我教的,完全学我。
乙 是啊?
甲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的戏一样。李盛藻——我给起的名字,在科班他排字排“盛”字儿。我说他叫“盛藻”,你就知道跟我学的啦。
乙 怎么?
甲 我叫“洗澡”嘛,他叫“剩澡”——我洗剩下他再洗!
乙 好嘛!俩人一个盆儿。
甲 我总在江南,江南一带。上海到过吗?
乙 到过。
甲 南京呢?
乙 到过。
甲 到南方你打听打听,海外天子、独树一帜——马喜藻,我!嘿,镇江,你打听吧!镇江大舞台,那剧场为我盖的。
乙 是啊?
甲 苏州,我。
乙 哎哟!
甲 我……杭州。
乙 好。
甲 ……芜湖……我,我快啦,快啦!
乙 快“呜呼”啦!要死了这位!
甲 我说我要死啊?我说我要死啊?
乙 不你说你快“呜呼”了吗?
甲 我快到芜湖那地方去啦。
乙 哦,到那儿演出。
甲 我现在不演出,我这些年不唱啦,气的!我生气,不唱啦。
乙 跟谁呀?生这么大气?
甲 这话!在哪儿,在上海。这年头你看,一九……我想想啊,一九四五年,你看这多少年了吧?
乙 日本降服那年。
甲 哎,对啦,日本降服,一九四五年。
乙 跟谁呀?生这么大气?
甲 那时候,我在那儿教……教票友,现在不叫业余吗?那时候就是票友。
乙 对对。
甲 国剧社。我呀,我在那儿当教练,教练,我教练。
乙 教练?足球啊?是排球啊?
甲 足球干吗呀?我唱戏!足球干什么?
乙 不是教练吗?你也唱戏?
甲 不是教练……我……我叫指挥,不叫指挥,我把场子,服务员把着。
乙 什么呀?
甲 把场子。
乙 把场子也不对呀。
甲 我得听,我得排!
乙 那叫导演。
甲 对,对!导演。我给你导演。(冲乙捣眼)
乙 别!一会儿瞎啦,你给我捣眼?
甲 我去那儿当导演,我给排戏。
乙 噢。
甲 票友跟我学。哎,很多票友,大伙儿要求我:“马老板,跟您学差不离,几年啦!每月给您这么些钱,天天管您饭,请你舞台上,你给看看。没见过您走台,您演两场,看看您舞台身段儿,跟您学学。”
乙 哎,让你演演。
甲 很多票友,要跟着学,要看看舞台经验,看看咱舞台表演,怎么办?
乙 那……演吧。
甲 唱吧。
乙 哎。
甲 咱不为赚钱,就为了让票友学。
乙 对对。
甲 演两天儿。
乙 在哪儿?
甲 在黄金。
乙 黄金大戏院?
甲 啊,礼拜六、礼拜演两天。晚场戏,演两个晚场。白天我不唱。白天我睡觉,白天我歇着。演两天,票友们学,这不订好了吗?该着你生气。
乙 怎么生气啦?
甲 唉!那年啊,那年哪,那个谁呀?小云儿啊!他呀,这番儿……
乙 哎?小云儿是谁呀?
甲 尚。
乙 尚小云?那是尚老板!还小云儿呢?
甲 尚小云呢,他这番儿啊,到上海,黄金戏院——他唱啦!又改他唱啦!把我气的。我正走剧院门口儿,我一看:黄金大戏院门口贴着这么大的大宇:“尚小云。星期六开始演
出。”我一看,哎?咱定好啦——礼拜六、礼拜呀?
乙 就是啊。
甲 怎么改啦?我问问这个经理,怎么办?
乙 得问问。
甲 我进这剧场,我上楼,找经理。“我说经理呢?经理呢?”经理在屋里坐着呢,“啊,来,来!进来!正要找你,不知你哪儿住。”
乙 这角儿,没准地儿。
甲 “你呀!听信儿。啊,现在先别来。”我说:“咱不是订好了吗?礼拜六,礼拜。”“啊,尚老板来啦。”我说:“哪个尚老板?”“尚小云——尚老板。”“那么我呢?”“你听信儿。”
乙 听信儿?
甲 我说:“听多咱的信儿啊?”“听信儿!多咱剧场接不着角儿,你来。”
乙 好嘛,这位是打补丁的。
甲 把我气的!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?你就信他呀?我非唱不可,我就唱!
乙 你非唱不可,那不给人尚老板开搅了吗?
甲 我搅和他干吗?我非得黄金大戏院呀?
乙 哎……对。
甲 我这艺术,我就一家剧场学的?真是!天坛舞台。
乙 天坛大舞台?嚯?最大的。
甲 对啦!本来定两天,我改三天。
乙 比他多一天。
甲 咱赌这气儿,戗这火。多演一天,我演三天。
乙 演三天。
甲 瞧他票价卖多少钱?跟他比着。打听打听,黄金戏院,他这怎么样?票价?一打听,尚小云那儿——八千块!
乙 八千?
甲 前排每座八千块!一九四五年。
乙 可不多。
甲 贵啦!大发啦!大发啦,高啦!价码高啦!
乙 买个烧饼还一百块钱呢,尚老板卖八千块儿?
甲 不值,不值。
乙 太贱啦。
甲 这不天坛舞台跟我商量了,咱这票价怎么定啊?我说那边多少钱?他说“八千。”那儿八千,一想啊,我这儿啊……甭犹豫,干脆!
乙 两千块钱儿!两千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。不为听戏,为喝茶……对不?
甲 谁呀?谁呀?你说谁呀这是?谁呀?说谁哪?
乙 说你呀!
甲 八千,那儿八千。
乙 八干那是尚老板。
甲 我,我多少钱?
乙 两千块钱,不少啦!
甲 我不值钱,我不如他?在哪儿?哪儿?哪儿,哪儿?你看见啦?看见啦!你听说的?你看见啦?你是听说啦?你看见啦?你听人说的还是你看见啦?
乙 我这么琢磨着。
甲 呸!要不这种人!你就不能搭理他,你不能理他呢!这儿还慢慢告诉你:八千、八千!他那儿八千!我两千?还带点儿好茶叶、管饭。我跟你要价,我算栽啦,我算栽跟头啦!
乙 哦?那您卖多少?
甲 卖多少钱呢?一万二!
乙 啊?前排一万二?
甲 前排干吗?不管前排,什么前排后排,一律一万二。前后排不对号。
乙 一万二?
甲 不对号入座,你赶上前排一万二,后排一万二。楼上、紧后边,照样一万二。
乙 嗬!这价码可高。
甲 就这价。听戏的,观众不在乎钱,看的是玩艺儿,听的是戏,咱三天戏码得硬。
乙 哎,头天是什么戏?
甲 啊?头天呢,《连环套》。
乙 《连环套》?
甲 “盗钩”。
乙 嘿!这戏好戏。
甲 嘿!《坐寨》、《盗马》、《拜山》、《盗钩》唱全啦!窦尔墩、尚小云来一个?尚小云来窦尔墩?
乙 来不了,来不了!
甲 噢,噢!完了吧!
乙 第二天呢?
甲 第二天呢,第二天我来一个《奇冤报》、《乌盆儿记》。
乙 老生戏?
甲 唱功戏。
乙 老生你也成啊?
甲 也行啊?也行啊!唱、打、做、念、翻,全活儿!
乙 老生,你去谁?
甲 《奇冤报》——老生!头天,我“窦尔墩”!《连环套》。
乙 别说窦尔墩!这《奇冤报》老生是谁啊?
甲 我唱功戏呀。
乙 是啊?去谁呀?
甲 第三天呢,我一想啊,我来一个……
乙 别,别三天!第二天。老生是谁?
甲 我知道。第二天啊,第二天啊,老生啊,谁呢?《乌盆记》嘛,他那个谁?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,做成盆儿嘛。
乙 对对,他叫什么名字?
甲 你瞧,(唱)有那公俺做了……
乙 行行。
甲 别忙,一会儿,这词儿就出来了。
乙 准问词儿啊?问你叫什么名字?叫什么?
甲 徐世昌。
乙 什么?
甲 徐世昌。
乙 徐世昌?刘世昌!
甲 对!刘世昌,刘世昌!对!我说成徐世昌了。刘世昌!
乙 徐世昌?那是大总统!
甲 刘世昌,对对!第二天我刘世昌。好!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!“红尤二楼”,“红尤二楼”!瞧我一个人的。我一个人顶下来。
乙 一个人顶下来吗?
甲 哎,怎么顶不下来呀?
乙 红油二楼?
甲 哎!
乙 三楼就不油啦?三楼还油吗?
甲 我这……我干吗?我油三楼干吗?
乙 你不说是“红油二楼”吗?
甲 这是那戏!这是大楼,什么楼……那戏!
乙 那是《红楼梦》,尤三姐、尤二姐!
甲 我知道,你甭管,我就来这个。头天的《连环套》,我唱晚场戏,白天我不唱。
乙 白天不唱?
甲 晚场戏。早晨,八点来钟,客满!剧场,坐满啦!
乙 晚场戏,早应该坐满啦!
甲 不对号啊,不对号入座,谁不得早去呀?赴前排座儿,得听得看哪。
乙 对对。
甲 都早去呀。观众去得早,八点,满座!我还没起呢,我睡得着着的,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,扒开门一看:嚄!我心里话!
乙 哎哎!等等!八点应就满了,你怎么知道的?
甲 这,正把我吵醒啦。
乙 把你吵醒啦?你在哪儿睡觉啊?
甲 后台。
乙 哈哈,后台睡觉?你住旅馆、饭店哪?
甲 我不住饭店,我就住后台。我总住后台,我总跟箱官儿在一块儿睡。叠衣裳,叠行头那个箱官儿。
乙 你干吗跟他在一块儿睡觉?
甲 我就为盖他的被卧。
乙 嗬!这角儿!连被卧都没有。
甲 不是没有,不是没有!
乙 有?
甲 我有钱不置这东西,我嫌麻烦,出门打行李卷儿,带着麻烦。我有钱,我多置行头,门帘、大抬杠我有七十多个。
乙 七十多个?
甲 哎。
乙 你改俩被卧好不好?
甲 管得着吗?我乐意呀!我乐意呀。刚顶中午十二点多钟,又来四百多位,买票。前边不能卖票啦,座满啦!没票了。“没票啦?不行!我们也得听啊!我们听马喜藻马老板,
我们不是这此地的。我们打南京来的、苏州、杭州来的、蚌埠来的、徐州来的、有石家庄来的、有邢台来的。”你瞧,这么多人,怎么办?没地方坐啦!“买站票吧!”“站票?行!”“一万二!”
乙 啊?站票也一万二?
甲 照样一万二。四百多位,愣屈尊大驾站着听,太好啦!太捧马喜藻啦!太捧戏啦!站着听,四百多位。刚站好,又来了,又来三百多位,非听不可。剧场经理说:“这怎么办
呢?站票都满啦,您买蹲票行吗”?“我们乐意,乐意”!
乙 蹲着?怎么蹲?
甲 人都上边宽底下窄呀,两位的空档蹲一个,两位的空档蹲一个。
乙 好嘛!受罪来啦!
甲 哎,刚蹲好,又来一百七十多位!
乙 一百七十多位?
甲 这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,直掉眼泪。“我听不着马喜藻,简直活不了啊。”
乙 哎,至于吗?这个!
甲 哎呀,经理心软啦,说“这怎么办?买挂票吧。对!挂!好,挂吧!”
乙 挂?怎么个挂票?
甲 就一棵绳子拴一个,一棵绳子拴一个,往墙上,往墙上一挂。
乙 好嘛!受罪来啦?
甲 挂票!挂一百七十多位!
乙 好!
甲 嗬!我心里这痛快!扮戏呀,窦尔墩!刚要打花脸儿啊!
乙 哎!那叫勾脸儿。
甲 我说勾脸儿怕你不懂!勾脸儿……勾眼儿?
乙 勾脸儿!
甲 刚要勾脸儿啊,从后台进来一个人,大高个,戴着黑眼镜儿,茶镜、墨镜,咱说不清楚啊,大个!“哦,辛苦,辛苦,辛苦!众位!哪位马老板?哪位是马老板马洗藻?哪位洗藻?”
乙 好嘛,找洗澡的!
甲 “我,我!我,我姓马!”“哦,你好!实在该来啦!少拜望!不知你哪儿住!”
乙 噢?谁呀这是?
甲 不认得。“你干吗的?唱戏的?不认识啊,贵姓?”“金、金少山。”“少山?”
乙 金少山来拜望?好!
甲 “啊,您找我?有事儿吗?”“没别的事儿,听说您贴《连环套》,非唱《窦尔墩》哪?你要唱窦尔墩,我就没能耐,江南、华北一带,我小小有‘蔓儿’,都知道我唱的不错。今儿听您这个,再听我那个,我一分钱不值啦!无论如何,你赏我点饭吃,我来窦尔墩。”
乙 他要来窦尔墩。
甲 我说:“你来窦尔墩,我呢?”“您来天霸?”“谁?”“我少山来窦尔墩,你来天霸。”
乙 天霸,你也行?
甲 也行?把“也”字去啦!就是“行”!我说:“好!你扮吧!我给你画脸儿。”“哟!你甭管,我自己来。”我说:“你来,好!”他窦尔墩,我来天霸。我说:“谁?瑞安!瑞安!”
乙 瑞安是谁呀?
甲 周瑞安,周瑞安都扮好天霸啦!我说:“你算了吧!你改弃权,我天霸。”我扮好了天霸了。我扒台帘儿一看:少山这……这窦尔墩啊!
乙 那是真好!
甲 一文没有啊。
乙 啊?
甲 《盗马》的那个地方,咱一看,抬手动脚,跟我那个完全、一点也不一样。
乙 是啊!他要跟你一样?他也没被卧啦!
甲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。他唱的《坐寨》,那摇头、晃脑地一唱,谁给他叫好?打他一出场,那台下的观众就嘀咕:“嘿!好啊,好!马老板呢?马喜藻!”“金少山哟?”“马老板?一定‘天霸’。”都憋着给黄天霸叫好!
乙 听你的。
甲 听着咱这一上场,你琢磨琢磨这模样!扮出天霸来怎么样?
乙 猴儿啊?
甲 好,句句落好。他不落好,咱还不落好?他唱的没要下来。咱那天,我嗓子也不知怎么啦!
乙 是啊?
甲 那天我不知道那天我吃了什么啦?那天,嗬!我嗓子这个亮啊!(学唱)“一马离了……”哎?不对。
乙 不是这词儿。
甲 这是《汾河湾》啦!
乙 什么《汾河湾》?
甲 《武家坡》啦!我是“宝马?”我是“保镖……保镖……”什么?
乙 “保镖路过马兰关”。
甲 哎?那天你听啦?
乙 我没听!
甲 听啦!听啦。
乙 我没听。
甲 没听,你怎么把我词儿给记住啦?
乙 你的词儿?
甲 我就这词儿。
乙 谁唱都这词儿。
甲 我就这词儿。我就这词儿,“保……”
乙 保镖!
甲 哦,对!(学唱)“保镖路过马兰关哪,啊……!”一落腔,底下这观众,连楼上、带楼下,哗!
乙 你瞧这好啊?
甲 全走啦!
乙 那还不走?
甲 骂着街地退票。
乙 好啊!
甲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?活该你走!你不懂艺术。咱这玩意儿,货卖有识家。
乙 对。
甲 真有一百七十多位没走!
乙 爱听?
甲 墙上挂着,走不了啦!
乙 走不了啦?
马三立 王凤山演出本
卖挂票
台词:
甲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,这个台词,跟其它的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。相声它这里头啊,它也有文言、也有成语、也有谚语、也有俗语、也有小市民语气,有地方语,那是很多。
乙 哎。
甲 戏剧就不是啦。话剧呢,它就不能说大白话,大部分是文言。京戏啊?那京剧,它就得呀,它单有京剧的台词。它就跟咱们普通话一样啦。
乙 是啊?
甲 哎。别忙——它就不能说“别忙!”“且慢!”——戏剧的“且慢!”。
乙 哎。别忙。
甲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,平常谁这么说?你刚走那儿—— “且慢”。可舞台里头懂——你听着戏,他说:“且慢!”听戏就是“别忙”,让他“打住”。“罢了!”是“得啦!”一见面,请安,“参见老大人”、“参见父母”、“参见爹爹”——“摆了”。咱平常不用,“老没见,你好啊?我给你请安!”“哎,得啦,得啦!”不能“罢了”!用不上。这舞台上它有舞台词——“罢了”!“且慢”,“呜呼呀”!“呜呼呀”是纳闷儿,“呜呼呀”!不信?“你待怎讲?——你再说一遍——你待怎讲?”
乙 哎。
甲 “嘟!”是急啦。“嗯?”是不乐意了,不乐意啦——“嗯?”“嘟!”急啦!这场戏见官儿,给官儿跪下,最好是:“呜呼呀!”这犯人准有好处,带上堂来——“给大人叩头!”“抬起头来!”“小人有罪不敢抬头。”“恕你无罪。”“谢大人!”官儿一瞧:“呜呼呀!”行啦。
乙 怎么?
甲 呜呼呀!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。详细审问,好啦。“嘟!”——坏啦!
乙 怎么?
甲 倒霉啦!“给大人叩头。”“抬起头来!”“有罪不敢抬头。”“恕你无罪!”“谢大人!”“嘟!”倒霉,准糟!
乙 生气了。
甲 那可不!这戏剧很深,下功夫最难。“唱、打、做、念、翻”,这个……这个舞台上……
乙 哦,您对京戏很有研究?
甲 研究干吗?你不认识我?你不常听戏。
乙 那你?
甲 你常听戏吗?京戏,你听不听吧?
乙 我从小就爱听戏。
甲 你要常听戏,你不能不认识我。你不能不认识我!你认识我吗?
乙 不认识啊?
甲 你看看!你细看看,哎呀……你们爱好京戏,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我。
乙 是啊?
甲 你怎么不认识我呢?
乙 您是哪一位?
甲 杨……
乙 杨?
甲 杨宝森!
乙 杨宝森?你是杨宝森?
甲 真是不认识,拿我……拿我当杨宝森。我不是!我不姓杨。谁杨宝森?拿我当杨宝森!我不是杨宝森哪。
乙 您是谁?
甲 提杨宝森这个人,你知道不知道?
乙 知道。
甲 我给他蹬三轮儿。这多少年了吧。
乙 多少年了?哎,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儿啊!
甲 那玩艺儿!
乙 那玩艺儿也是蹬三轮儿啊。
甲 他蹬三轮儿,蹬我。
乙 哦,蹬你!拿你当三轮儿啦?
甲 拿你当三轮啦!我坐……我坐那儿,蹬三轮儿那蹬着,后来我让他,“你蹬宝森吧!”宝森净闹病,车是我的,我送给宝森。
乙 啊,送给他了。
甲 我不姓杨。
乙 哦!您是?
甲 马!北京你打听打听!北京你打听打听,唱戏的马老板!那谁不知道啊?
乙 哦,北京马老板?马连良?
甲 马连良干吗?马连良是我们本家,我们都一家子。
乙 哦,一家子。
甲 马连良是“连”字儿的。
乙 对。
甲 “富连成”,他排字排“连”字的!我们科班儿,那时候叫“喜连成”,听说过吗?
乙 听说过。
甲 “喜连成”!哎,我们“喜”字,雷喜福?知道吧?
乙 雷喜福,大师兄?
甲 哎,对。
乙 知道。
甲 我们一块儿的。这还用说吗?侯喜瑞知道吗?
乙 知道哇。
甲 侯喜瑞——“喜”字嘛,陈喜星、康喜寿、魏喜奎……没有魏喜奎,魏喜奎她改大鼓啦。
乙 没改!一起就唱大鼓的。
甲 不是魏喜奎,什么“喜奎”我忘了。
乙 哎,刘喜奎。
甲 刘喜奎,对。反正我们都“喜”字儿的。
乙 哦,您叫?
甲 喜藻。
乙 洗……我修脚。
甲 修脚干吗?
乙 你洗澡干吗?你那儿洗完啦,我这儿……。
甲 喜!排“喜”字儿那个“喜”呀。
乙 那个“喜”呀?
甲 不是洗澡的那个“洗”。道喜、福禄寿喜的“喜”。
乙 噢!澡?
甲 藻是那个……这个字还说不上来。
乙 他连名字都说不上来。
甲 草字头那个……我想想草字头那个。
乙 李盛藻的那个“藻”。
甲 哎,你要是不提,我还把他给忘啦!李盛藻,听过吗?
乙 听过。
甲 唱的怎么样?
乙 好啊。
甲 别捧,别捧!别捧,别捧!说实在的,李盛藻唱得行吗?
乙 不错。
甲 你认为怎么样?
乙 都认为不错。
甲 服吗?
乙 服!
甲 那就完了,那咱就没杠抬了。你服,就完啦。那我就……行啦。
乙 我服李盛藻,碍着你什么啦?
甲 你要服李盛藻就行啦,
乙 怎么啦?
甲 你认为盛藻好,那就成!我痛快。
乙 与你何干?
甲 他跟我学的。
乙 李盛藻跟你学的?
甲 有人听过吧?李盛藻唱的怎么样?他完全学我,也就是我教戏。我当初在科班时候,我给他排戏,那都是我教的,完全学我。
乙 是啊?
甲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的戏一样。李盛藻——我给起的名字,在科班他排字排“盛”字儿。我说他叫“盛藻”,你就知道跟我学的啦。
乙 怎么?
甲 我叫“洗澡”嘛,他叫“剩澡”——我洗剩下他再洗!
乙 好嘛!俩人一个盆儿。
甲 我总在江南,江南一带。上海到过吗?
乙 到过。
甲 南京呢?
乙 到过。
甲 到南方你打听打听,海外天子、独树一帜——马喜藻,我!嘿,镇江,你打听吧!镇江大舞台,那剧场为我盖的。
乙 是啊?
甲 苏州,我。
乙 哎哟!
甲 我……杭州。
乙 好。
甲 ……芜湖……我,我快啦,快啦!
乙 快“呜呼”啦!要死了这位!
甲 我说我要死啊?我说我要死啊?
乙 不你说你快“呜呼”了吗?
甲 我快到芜湖那地方去啦。
乙 哦,到那儿演出。
甲 我现在不演出,我这些年不唱啦,气的!我生气,不唱啦。
乙 跟谁呀?生这么大气?
甲 这话!在哪儿,在上海。这年头你看,一九……我想想啊,一九四五年,你看这多少年了吧?
乙 日本降服那年。
甲 哎,对啦,日本降服,一九四五年。
乙 跟谁呀?生这么大气?
甲 那时候,我在那儿教……教票友,现在不叫业余吗?那时候就是票友。
乙 对对。
甲 国剧社。我呀,我在那儿当教练,教练,我教练。
乙 教练?足球啊?是排球啊?
甲 足球干吗呀?我唱戏!足球干什么?
乙 不是教练吗?你也唱戏?
甲 不是教练……我……我叫指挥,不叫指挥,我把场子,服务员把着。
乙 什么呀?
甲 把场子。
乙 把场子也不对呀。
甲 我得听,我得排!
乙 那叫导演。
甲 对,对!导演。我给你导演。(冲乙捣眼)
乙 别!一会儿瞎啦,你给我捣眼?
甲 我去那儿当导演,我给排戏。
乙 噢。
甲 票友跟我学。哎,很多票友,大伙儿要求我:“马老板,跟您学差不离,几年啦!每月给您这么些钱,天天管您饭,请你舞台上,你给看看。没见过您走台,您演两场,看看您舞台身段儿,跟您学学。”
乙 哎,让你演演。
甲 很多票友,要跟着学,要看看舞台经验,看看咱舞台表演,怎么办?
乙 那……演吧。
甲 唱吧。
乙 哎。
甲 咱不为赚钱,就为了让票友学。
乙 对对。
甲 演两天儿。
乙 在哪儿?
甲 在黄金。
乙 黄金大戏院?
甲 啊,礼拜六、礼拜演两天。晚场戏,演两个晚场。白天我不唱。白天我睡觉,白天我歇着。演两天,票友们学,这不订好了吗?该着你生气。
乙 怎么生气啦?
甲 唉!那年啊,那年哪,那个谁呀?小云儿啊!他呀,这番儿……
乙 哎?小云儿是谁呀?
甲 尚。
乙 尚小云?那是尚老板!还小云儿呢?
甲 尚小云呢,他这番儿啊,到上海,黄金戏院——他唱啦!又改他唱啦!把我气的。我正走剧院门口儿,我一看:黄金大戏院门口贴着这么大的大宇:“尚小云。星期六开始演
出。”我一看,哎?咱定好啦——礼拜六、礼拜呀?
乙 就是啊。
甲 怎么改啦?我问问这个经理,怎么办?
乙 得问问。
甲 我进这剧场,我上楼,找经理。“我说经理呢?经理呢?”经理在屋里坐着呢,“啊,来,来!进来!正要找你,不知你哪儿住。”
乙 这角儿,没准地儿。
甲 “你呀!听信儿。啊,现在先别来。”我说:“咱不是订好了吗?礼拜六,礼拜。”“啊,尚老板来啦。”我说:“哪个尚老板?”“尚小云——尚老板。”“那么我呢?”“你听信儿。”
乙 听信儿?
甲 我说:“听多咱的信儿啊?”“听信儿!多咱剧场接不着角儿,你来。”
乙 好嘛,这位是打补丁的。
甲 把我气的!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?你就信他呀?我非唱不可,我就唱!
乙 你非唱不可,那不给人尚老板开搅了吗?
甲 我搅和他干吗?我非得黄金大戏院呀?
乙 哎……对。
甲 我这艺术,我就一家剧场学的?真是!天坛舞台。
乙 天坛大舞台?嚯?最大的。
甲 对啦!本来定两天,我改三天。
乙 比他多一天。
甲 咱赌这气儿,戗这火。多演一天,我演三天。
乙 演三天。
甲 瞧他票价卖多少钱?跟他比着。打听打听,黄金戏院,他这怎么样?票价?一打听,尚小云那儿——八千块!
乙 八千?
甲 前排每座八千块!一九四五年。
乙 可不多。
甲 贵啦!大发啦!大发啦,高啦!价码高啦!
乙 买个烧饼还一百块钱呢,尚老板卖八千块儿?
甲 不值,不值。
乙 太贱啦。
甲 这不天坛舞台跟我商量了,咱这票价怎么定啊?我说那边多少钱?他说“八千。”那儿八千,一想啊,我这儿啊……甭犹豫,干脆!
乙 两千块钱儿!两千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。不为听戏,为喝茶……对不?
甲 谁呀?谁呀?你说谁呀这是?谁呀?说谁哪?
乙 说你呀!
甲 八千,那儿八千。
乙 八干那是尚老板。
甲 我,我多少钱?
乙 两千块钱,不少啦!
甲 我不值钱,我不如他?在哪儿?哪儿?哪儿,哪儿?你看见啦?看见啦!你听说的?你看见啦?你是听说啦?你看见啦?你听人说的还是你看见啦?
乙 我这么琢磨着。
甲 呸!要不这种人!你就不能搭理他,你不能理他呢!这儿还慢慢告诉你:八千、八千!他那儿八千!我两千?还带点儿好茶叶、管饭。我跟你要价,我算栽啦,我算栽跟头啦!
乙 哦?那您卖多少?
甲 卖多少钱呢?一万二!
乙 啊?前排一万二?
甲 前排干吗?不管前排,什么前排后排,一律一万二。前后排不对号。
乙 一万二?
甲 不对号入座,你赶上前排一万二,后排一万二。楼上、紧后边,照样一万二。
乙 嗬!这价码可高。
甲 就这价。听戏的,观众不在乎钱,看的是玩艺儿,听的是戏,咱三天戏码得硬。
乙 哎,头天是什么戏?
甲 啊?头天呢,《连环套》。
乙 《连环套》?
甲 “盗钩”。
乙 嘿!这戏好戏。
甲 嘿!《坐寨》、《盗马》、《拜山》、《盗钩》唱全啦!窦尔墩、尚小云来一个?尚小云来窦尔墩?
乙 来不了,来不了!
甲 噢,噢!完了吧!
乙 第二天呢?
甲 第二天呢,第二天我来一个《奇冤报》、《乌盆儿记》。
乙 老生戏?
甲 唱功戏。
乙 老生你也成啊?
甲 也行啊?也行啊!唱、打、做、念、翻,全活儿!
乙 老生,你去谁?
甲 《奇冤报》——老生!头天,我“窦尔墩”!《连环套》。
乙 别说窦尔墩!这《奇冤报》老生是谁啊?
甲 我唱功戏呀。
乙 是啊?去谁呀?
甲 第三天呢,我一想啊,我来一个……
乙 别,别三天!第二天。老生是谁?
甲 我知道。第二天啊,第二天啊,老生啊,谁呢?《乌盆记》嘛,他那个谁?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,做成盆儿嘛。
乙 对对,他叫什么名字?
甲 你瞧,(唱)有那公俺做了……
乙 行行。
甲 别忙,一会儿,这词儿就出来了。
乙 准问词儿啊?问你叫什么名字?叫什么?
甲 徐世昌。
乙 什么?
甲 徐世昌。
乙 徐世昌?刘世昌!
甲 对!刘世昌,刘世昌!对!我说成徐世昌了。刘世昌!
乙 徐世昌?那是大总统!
甲 刘世昌,对对!第二天我刘世昌。好!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!“红尤二楼”,“红尤二楼”!瞧我一个人的。我一个人顶下来。
乙 一个人顶下来吗?
甲 哎,怎么顶不下来呀?
乙 红油二楼?
甲 哎!
乙 三楼就不油啦?三楼还油吗?
甲 我这……我干吗?我油三楼干吗?
乙 你不说是“红油二楼”吗?
甲 这是那戏!这是大楼,什么楼……那戏!
乙 那是《红楼梦》,尤三姐、尤二姐!
甲 我知道,你甭管,我就来这个。头天的《连环套》,我唱晚场戏,白天我不唱。
乙 白天不唱?
甲 晚场戏。早晨,八点来钟,客满!剧场,坐满啦!
乙 晚场戏,早应该坐满啦!
甲 不对号啊,不对号入座,谁不得早去呀?赴前排座儿,得听得看哪。
乙 对对。
甲 都早去呀。观众去得早,八点,满座!我还没起呢,我睡得着着的,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,扒开门一看:嚄!我心里话!
乙 哎哎!等等!八点应就满了,你怎么知道的?
甲 这,正把我吵醒啦。
乙 把你吵醒啦?你在哪儿睡觉啊?
甲 后台。
乙 哈哈,后台睡觉?你住旅馆、饭店哪?
甲 我不住饭店,我就住后台。我总住后台,我总跟箱官儿在一块儿睡。叠衣裳,叠行头那个箱官儿。
乙 你干吗跟他在一块儿睡觉?
甲 我就为盖他的被卧。
乙 嗬!这角儿!连被卧都没有。
甲 不是没有,不是没有!
乙 有?
甲 我有钱不置这东西,我嫌麻烦,出门打行李卷儿,带着麻烦。我有钱,我多置行头,门帘、大抬杠我有七十多个。
乙 七十多个?
甲 哎。
乙 你改俩被卧好不好?
甲 管得着吗?我乐意呀!我乐意呀。刚顶中午十二点多钟,又来四百多位,买票。前边不能卖票啦,座满啦!没票了。“没票啦?不行!我们也得听啊!我们听马喜藻马老板,
我们不是这此地的。我们打南京来的、苏州、杭州来的、蚌埠来的、徐州来的、有石家庄来的、有邢台来的。”你瞧,这么多人,怎么办?没地方坐啦!“买站票吧!”“站票?行!”“一万二!”
乙 啊?站票也一万二?
甲 照样一万二。四百多位,愣屈尊大驾站着听,太好啦!太捧马喜藻啦!太捧戏啦!站着听,四百多位。刚站好,又来了,又来三百多位,非听不可。剧场经理说:“这怎么办
呢?站票都满啦,您买蹲票行吗”?“我们乐意,乐意”!
乙 蹲着?怎么蹲?
甲 人都上边宽底下窄呀,两位的空档蹲一个,两位的空档蹲一个。
乙 好嘛!受罪来啦!
甲 哎,刚蹲好,又来一百七十多位!
乙 一百七十多位?
甲 这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,直掉眼泪。“我听不着马喜藻,简直活不了啊。”
乙 哎,至于吗?这个!
甲 哎呀,经理心软啦,说“这怎么办?买挂票吧。对!挂!好,挂吧!”
乙 挂?怎么个挂票?
甲 就一棵绳子拴一个,一棵绳子拴一个,往墙上,往墙上一挂。
乙 好嘛!受罪来啦?
甲 挂票!挂一百七十多位!
乙 好!
甲 嗬!我心里这痛快!扮戏呀,窦尔墩!刚要打花脸儿啊!
乙 哎!那叫勾脸儿。
甲 我说勾脸儿怕你不懂!勾脸儿……勾眼儿?
乙 勾脸儿!
甲 刚要勾脸儿啊,从后台进来一个人,大高个,戴着黑眼镜儿,茶镜、墨镜,咱说不清楚啊,大个!“哦,辛苦,辛苦,辛苦!众位!哪位马老板?哪位是马老板马洗藻?哪位洗藻?”
乙 好嘛,找洗澡的!
甲 “我,我!我,我姓马!”“哦,你好!实在该来啦!少拜望!不知你哪儿住!”
乙 噢?谁呀这是?
甲 不认得。“你干吗的?唱戏的?不认识啊,贵姓?”“金、金少山。”“少山?”
乙 金少山来拜望?好!
甲 “啊,您找我?有事儿吗?”“没别的事儿,听说您贴《连环套》,非唱《窦尔墩》哪?你要唱窦尔墩,我就没饭啦!虽然说我没能耐,江南、华北一带,我小小有‘蔓儿’,都知道我唱的不错。今儿听您这个,再听我那个,我一分钱不值啦!无论如何,你赏我点饭吃,我来窦尔墩。”
乙 他要来窦尔墩。
甲 我说:“你来窦尔墩,我呢?”“您来天霸?”“谁?”“我少山来窦尔墩,你来天霸。”
乙 天霸,你也行?
甲 也行?把“也”字去啦!就是“行”!我说:“好!你扮吧!我给你画脸儿。”“哟!你甭管,我自己来。”我说:“你来,好!”他窦尔墩,我来天霸。我说:“谁?瑞安!瑞安!”
乙 瑞安是谁呀?
甲 周瑞安,周瑞安都扮好天霸啦!我说:“你算了吧!你改弃权,我天霸。”我扮好了天霸了。我扒台帘儿一看:少山这……这窦尔墩啊!
乙 那是真好!
甲 一文没有啊。
乙 啊?
甲 《盗马》的那个地方,咱一看,抬手动脚,跟我那个完全、一点也不一样。
乙 是啊!他要跟你一样?他也没被卧啦!
甲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。他唱的《坐寨》,那摇头、晃脑地一唱,谁给他叫好?打他一出场,那台下的观众就嘀咕:“嘿!好啊,好!马老板呢?马喜藻!”“金少山哟?”“马老板?一定‘天霸’。”都憋着给黄天霸叫好!
乙 听你的。
甲 听着咱这一上场,你琢磨琢磨这模样!扮出天霸来怎么样?
乙 猴儿啊?
甲 好,句句落好。他不落好,咱还不落好?他唱的没要下来。咱那天,我嗓子也不知怎么啦!
乙 是啊?
甲 那天我不知道那天我吃了什么啦?那天,嗬!我嗓子这个亮啊!(学唱)“一马离了……”哎?不对。
乙 不是这词儿。
甲 这是《汾河湾》啦!
乙 什么《汾河湾》?
甲 《武家坡》啦!我是“宝马?”我是“保镖……保镖……”什么?
乙 “保镖路过马兰关”。
甲 哎?那天你听啦?
乙 我没听!
甲 听啦!听啦。
乙 我没听。
甲 没听,你怎么把我词儿给记住啦?
乙 你的词儿?
甲 我就这词儿。
乙 谁唱都这词儿。
甲 我就这词儿。我就这词儿,“保……”
乙 保镖!
甲 哦,对!(学唱)“保镖路过马兰关哪,啊……!”一落腔,底下这观众,连楼上、带楼下,哗!
乙 你瞧这好啊?
甲 全走啦!
乙 那还不走?
甲 骂着街地退票。
乙 好啊!
甲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?活该你走!你不懂艺术。咱这玩意儿,货卖有识家。
乙 对。
甲 真有一百七十多位没走!
乙 爱听?
甲 墙上挂着,走不了啦!
乙 走不了啦?
马三立 王凤山演出本
打电话,13课
~
#韦婕肺# 求小学生(五年级)3 - 4人搞笑小品,要短的! -
(17358519549): 草船借箭缩写400字(七) 草船借箭缩写 周瑜很妒忌诸葛亮(字孔明)的才干.因水中交战需要箭,周瑜要诸葛亮在十天内负责赶造十万支箭,哪知诸葛亮只要三天,还愿立下军令状,完不成任务甘受处罚.周瑜想,三天不可能造出十万支箭,...
#韦婕肺# 跪求小学五年级的5人搞笑小品,,快到元旦了快点谢谢 -
(17358519549): 《新笑林》
#韦婕肺# 有没有适合小学生演的爆笑小品?急!急!!急!!! -
(17358519549): 搞笑课本剧《乌鸦与狐狸 角色:乌鸦甲,乌鸦乙,(文中以甲乙代替),狐狸. 旁白:这是一个发生在猪肉价格猛涨时期的真实故事,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森林里,乌鸦小姐收到了好心人寄来的两斤猪肉~~~~~ (舞台灯光溅亮,甲乙惊喜的蹲着...
#韦婕肺# 小学生四人表演的爆笑小品 -
(17358519549): 偷车情缘(校园小品) 人物:男偷T,女偷T,男生S,女生S 场景:长椅边 内容:男偷背包上:天气好,抖精神,拿上家伙跨出门,不靠家,不求人,富裕全都靠个人! 你问我是做什么?嘿嘿!(拿出背包里的一大串钥匙)偷车神! 女T上:...
#韦婕肺# 有没有什么搞笑的小品,适合小学生的小品,而且要5个人的. -
(17358519549): 清早去买鱼,不料因为价格和老板打起来了.混战之中,他抓起冻鱼对着我就是一顿狂打,我瞬间就被打蒙,那一刻,什么都不知道了,只感觉冷冷的冰鱼在脸上胡乱地拍...
#韦婕肺# 五年级适合演的相声、、小品 -
(17358519549): 发了一个相声《你爷爷我爷爷》,希望有用. 你爷爷 我爷爷甲:问你个事?乙:什么事啊?甲:你认识我爷爷吗?乙:噢!你爷爷啊!甲:熟悉吧?乙:不认识!甲:....我认识.乙:唉呀,真了不起啊,你连你爷爷都认识.甲:要不人家说我智...
#韦婕肺# 小学生5人小品剧本,要搞笑的,爆笑最好,注意(五人)小品.... 六一马上要到了,我们小学生要表演小品.急 -
(17358519549): 我觉得5个人可以演啦啦啦德玛西亚第一集,正好5个人,而且好玩,也可以出一些有创意的.爆笑校园和阿衰上的一些好玩的行为或语音可以融入.
#韦婕肺# 小学生演的小品搞笑 -
(17358519549): 人物:王婆甲、乙、丙;顾客子、丑、寅. 地点:吹街炒市. 时间:离永远没多远. 王婆甲:快来买,玉女牌西瓜,保甜保熟保沙瓤哩! 顾客子(举瓜敲了敲):你这瓜不熟吧? 王婆甲:熟大发就娄了.再者说,熟的档期已满,你请得动吗?...
台词:
甲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,这个台词,跟其它的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。相声它这里头啊,它也有文言、也有成语、也有谚语、也有俗语、也有小市民语气,有地方语,那是很多。
乙 哎。
甲 戏剧就不是啦。话剧呢,它就不能说大白话,大部分是文言。京戏啊?那京剧,它就得呀,它单有京剧的台词。它就跟咱们普通话一样啦。
乙 是啊?
甲 哎。别忙——它就不能说“别忙!”“且慢!”——戏剧的“且慢!”。
乙 哎。别忙。
甲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,平常谁这么说?你刚走那儿—— “且慢”。可舞台里头懂——你听着戏,他说:“且慢!”听戏就是“别忙”,让他“打住”。“罢了!”是“得啦!”一见面,请安,“参见老大人”、“参见父母”、“参见爹爹”——“摆了”。咱平常不用,“老没见,你好啊?我给你请安!”“哎,得啦,得啦!”不能“罢了”!用不上。这舞台上它有舞台词——“罢了”!“且慢”,“呜呼呀”!“呜呼呀”是纳闷儿,“呜呼呀”!不信?“你待怎讲?——你再说一遍——你待怎讲?”
乙 哎。
甲 “嘟!”是急啦。“嗯?”是不乐意了,不乐意啦——“嗯?”“嘟!”急啦!这场戏见官儿,给官儿跪下,最好是:“呜呼呀!”这犯人准有好处,带上堂来——“给大人叩头!”“抬起头来!”“小人有罪不敢抬头。”“恕你无罪。”“谢大人!”官儿一瞧:“呜呼呀!”行啦。
乙 怎么?
甲 呜呼呀!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。详细审问,好啦。“嘟!”——坏啦!
乙 怎么?
甲 倒霉啦!“给大人叩头。”“抬起头来!”“有罪不敢抬头。”“恕你无罪!”“谢大人!”“嘟!”倒霉,准糟!
乙 生气了。
甲 那可不!这戏剧很深,下功夫最难。“唱、打、做、念、翻”,这个……这个舞台上……
乙 哦,您对京戏很有研究?
甲 研究干吗?你不认识我?你不常听戏。
乙 那你?
甲 你常听戏吗?京戏,你听不听吧?
乙 我从小就爱听戏。
甲 你要常听戏,你不能不认识我。你不能不认识我!你认识我吗?
乙 不认识啊?
甲 你看看!你细看看,哎呀……你们爱好京戏,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我。
乙 是啊?
甲 你怎么不认识我呢?
乙 您是哪一位?
甲 杨……
乙 杨?
甲 杨宝森!
乙 杨宝森?你是杨宝森?
甲 真是不认识,拿我……拿我当杨宝森。我不是!我不姓杨。谁杨宝森?拿我当杨宝森!我不是杨宝森哪。
乙 您是谁?
甲 提杨宝森这个人,你知道不知道?
乙 知道。
甲 我给他蹬三轮儿。这多少年了吧。
乙 多少年了?哎,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儿啊!
甲 那玩艺儿!
乙 那玩艺儿也是蹬三轮儿啊。
甲 他蹬三轮儿,蹬我。
乙 哦,蹬你!拿你当三轮儿啦?
甲 拿你当三轮啦!我坐……我坐那儿,蹬三轮儿那蹬着,后来我让他,“你蹬宝森吧!”宝森净闹病,车是我的,我送给宝森。
乙 啊,送给他了。
甲 我不姓杨。
乙 哦!您是?
甲 马!北京你打听打听!北京你打听打听,唱戏的马老板!那谁不知道啊?
乙 哦,北京马老板?马连良?
甲 马连良干吗?马连良是我们本家,我们都一家子。
乙 哦,一家子。
甲 马连良是“连”字儿的。
乙 对。
甲 “富连成”,他排字排“连”字的!我们科班儿,那时候叫“喜连成”,听说过吗?
乙 听说过。
甲 “喜连成”!哎,我们“喜”字,雷喜福?知道吧?
乙 雷喜福,大师兄?
甲 哎,对。
乙 知道。
甲 我们一块儿的。这还用说吗?侯喜瑞知道吗?
乙 知道哇。
甲 侯喜瑞——“喜”字嘛,陈喜星、康喜寿、魏喜奎……没有魏喜奎,魏喜奎她改大鼓啦。
乙 没改!一起就唱大鼓的。
甲 不是魏喜奎,什么“喜奎”我忘了。
乙 哎,刘喜奎。
甲 刘喜奎,对。反正我们都“喜”字儿的。
乙 哦,您叫?
甲 喜藻。
乙 洗……我修脚。
甲 修脚干吗?
乙 你洗澡干吗?你那儿洗完啦,我这儿……。
甲 喜!排“喜”字儿那个“喜”呀。
乙 那个“喜”呀?
甲 不是洗澡的那个“洗”。道喜、福禄寿喜的“喜”。
乙 噢!澡?
甲 藻是那个……这个字还说不上来。
乙 他连名字都说不上来。
甲 草字头那个……我想想草字头那个。
乙 李盛藻的那个“藻”。
甲 哎,你要是不提,我还把他给忘啦!李盛藻,听过吗?
乙 听过。
甲 唱的怎么样?
乙 好啊。
甲 别捧,别捧!别捧,别捧!说实在的,李盛藻唱得行吗?
乙 不错。
甲 你认为怎么样?
乙 都认为不错。
甲 服吗?
乙 服!
甲 那就完了,那咱就没杠抬了。你服,就完啦。那我就……行啦。
乙 我服李盛藻,碍着你什么啦?
甲 你要服李盛藻就行啦,
乙 怎么啦?
甲 你认为盛藻好,那就成!我痛快。
乙 与你何干?
甲 他跟我学的。
乙 李盛藻跟你学的?
甲 有人听过吧?李盛藻唱的怎么样?他完全学我,也就是我教戏。我当初在科班时候,我给他排戏,那都是我教的,完全学我。
乙 是啊?
甲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的戏一样。李盛藻——我给起的名字,在科班他排字排“盛”字儿。我说他叫“盛藻”,你就知道跟我学的啦。
乙 怎么?
甲 我叫“洗澡”嘛,他叫“剩澡”——我洗剩下他再洗!
乙 好嘛!俩人一个盆儿。
甲 我总在江南,江南一带。上海到过吗?
乙 到过。
甲 南京呢?
乙 到过。
甲 到南方你打听打听,海外天子、独树一帜——马喜藻,我!嘿,镇江,你打听吧!镇江大舞台,那剧场为我盖的。
乙 是啊?
甲 苏州,我。
乙 哎哟!
甲 我……杭州。
乙 好。
甲 ……芜湖……我,我快啦,快啦!
乙 快“呜呼”啦!要死了这位!
甲 我说我要死啊?我说我要死啊?
乙 不你说你快“呜呼”了吗?
甲 我快到芜湖那地方去啦。
乙 哦,到那儿演出。
甲 我现在不演出,我这些年不唱啦,气的!我生气,不唱啦。
乙 跟谁呀?生这么大气?
甲 这话!在哪儿,在上海。这年头你看,一九……我想想啊,一九四五年,你看这多少年了吧?
乙 日本降服那年。
甲 哎,对啦,日本降服,一九四五年。
乙 跟谁呀?生这么大气?
甲 那时候,我在那儿教……教票友,现在不叫业余吗?那时候就是票友。
乙 对对。
甲 国剧社。我呀,我在那儿当教练,教练,我教练。
乙 教练?足球啊?是排球啊?
甲 足球干吗呀?我唱戏!足球干什么?
乙 不是教练吗?你也唱戏?
甲 不是教练……我……我叫指挥,不叫指挥,我把场子,服务员把着。
乙 什么呀?
甲 把场子。
乙 把场子也不对呀。
甲 我得听,我得排!
乙 那叫导演。
甲 对,对!导演。我给你导演。(冲乙捣眼)
乙 别!一会儿瞎啦,你给我捣眼?
甲 我去那儿当导演,我给排戏。
乙 噢。
甲 票友跟我学。哎,很多票友,大伙儿要求我:“马老板,跟您学差不离,几年啦!每月给您这么些钱,天天管您饭,请你舞台上,你给看看。没见过您走台,您演两场,看看您舞台身段儿,跟您学学。”
乙 哎,让你演演。
甲 很多票友,要跟着学,要看看舞台经验,看看咱舞台表演,怎么办?
乙 那……演吧。
甲 唱吧。
乙 哎。
甲 咱不为赚钱,就为了让票友学。
乙 对对。
甲 演两天儿。
乙 在哪儿?
甲 在黄金。
乙 黄金大戏院?
甲 啊,礼拜六、礼拜演两天。晚场戏,演两个晚场。白天我不唱。白天我睡觉,白天我歇着。演两天,票友们学,这不订好了吗?该着你生气。
乙 怎么生气啦?
甲 唉!那年啊,那年哪,那个谁呀?小云儿啊!他呀,这番儿……
乙 哎?小云儿是谁呀?
甲 尚。
乙 尚小云?那是尚老板!还小云儿呢?
甲 尚小云呢,他这番儿啊,到上海,黄金戏院——他唱啦!又改他唱啦!把我气的。我正走剧院门口儿,我一看:黄金大戏院门口贴着这么大的大宇:“尚小云。星期六开始演
出。”我一看,哎?咱定好啦——礼拜六、礼拜呀?
乙 就是啊。
甲 怎么改啦?我问问这个经理,怎么办?
乙 得问问。
甲 我进这剧场,我上楼,找经理。“我说经理呢?经理呢?”经理在屋里坐着呢,“啊,来,来!进来!正要找你,不知你哪儿住。”
乙 这角儿,没准地儿。
甲 “你呀!听信儿。啊,现在先别来。”我说:“咱不是订好了吗?礼拜六,礼拜。”“啊,尚老板来啦。”我说:“哪个尚老板?”“尚小云——尚老板。”“那么我呢?”“你听信儿。”
乙 听信儿?
甲 我说:“听多咱的信儿啊?”“听信儿!多咱剧场接不着角儿,你来。”
乙 好嘛,这位是打补丁的。
甲 把我气的!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?你就信他呀?我非唱不可,我就唱!
乙 你非唱不可,那不给人尚老板开搅了吗?
甲 我搅和他干吗?我非得黄金大戏院呀?
乙 哎……对。
甲 我这艺术,我就一家剧场学的?真是!天坛舞台。
乙 天坛大舞台?嚯?最大的。
甲 对啦!本来定两天,我改三天。
乙 比他多一天。
甲 咱赌这气儿,戗这火。多演一天,我演三天。
乙 演三天。
甲 瞧他票价卖多少钱?跟他比着。打听打听,黄金戏院,他这怎么样?票价?一打听,尚小云那儿——八千块!
乙 八千?
甲 前排每座八千块!一九四五年。
乙 可不多。
甲 贵啦!大发啦!大发啦,高啦!价码高啦!
乙 买个烧饼还一百块钱呢,尚老板卖八千块儿?
甲 不值,不值。
乙 太贱啦。
甲 这不天坛舞台跟我商量了,咱这票价怎么定啊?我说那边多少钱?他说“八千。”那儿八千,一想啊,我这儿啊……甭犹豫,干脆!
乙 两千块钱儿!两千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。不为听戏,为喝茶……对不?
甲 谁呀?谁呀?你说谁呀这是?谁呀?说谁哪?
乙 说你呀!
甲 八千,那儿八千。
乙 八干那是尚老板。
甲 我,我多少钱?
乙 两千块钱,不少啦!
甲 我不值钱,我不如他?在哪儿?哪儿?哪儿,哪儿?你看见啦?看见啦!你听说的?你看见啦?你是听说啦?你看见啦?你听人说的还是你看见啦?
乙 我这么琢磨着。
甲 呸!要不这种人!你就不能搭理他,你不能理他呢!这儿还慢慢告诉你:八千、八千!他那儿八千!我两千?还带点儿好茶叶、管饭。我跟你要价,我算栽啦,我算栽跟头啦!
乙 哦?那您卖多少?
甲 卖多少钱呢?一万二!
乙 啊?前排一万二?
甲 前排干吗?不管前排,什么前排后排,一律一万二。前后排不对号。
乙 一万二?
甲 不对号入座,你赶上前排一万二,后排一万二。楼上、紧后边,照样一万二。
乙 嗬!这价码可高。
甲 就这价。听戏的,观众不在乎钱,看的是玩艺儿,听的是戏,咱三天戏码得硬。
乙 哎,头天是什么戏?
甲 啊?头天呢,《连环套》。
乙 《连环套》?
甲 “盗钩”。
乙 嘿!这戏好戏。
甲 嘿!《坐寨》、《盗马》、《拜山》、《盗钩》唱全啦!窦尔墩、尚小云来一个?尚小云来窦尔墩?
乙 来不了,来不了!
甲 噢,噢!完了吧!
乙 第二天呢?
甲 第二天呢,第二天我来一个《奇冤报》、《乌盆儿记》。
乙 老生戏?
甲 唱功戏。
乙 老生你也成啊?
甲 也行啊?也行啊!唱、打、做、念、翻,全活儿!
乙 老生,你去谁?
甲 《奇冤报》——老生!头天,我“窦尔墩”!《连环套》。
乙 别说窦尔墩!这《奇冤报》老生是谁啊?
甲 我唱功戏呀。
乙 是啊?去谁呀?
甲 第三天呢,我一想啊,我来一个……
乙 别,别三天!第二天。老生是谁?
甲 我知道。第二天啊,第二天啊,老生啊,谁呢?《乌盆记》嘛,他那个谁?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,做成盆儿嘛。
乙 对对,他叫什么名字?
甲 你瞧,(唱)有那公俺做了……
乙 行行。
甲 别忙,一会儿,这词儿就出来了。
乙 准问词儿啊?问你叫什么名字?叫什么?
甲 徐世昌。
乙 什么?
甲 徐世昌。
乙 徐世昌?刘世昌!
甲 对!刘世昌,刘世昌!对!我说成徐世昌了。刘世昌!
乙 徐世昌?那是大总统!
甲 刘世昌,对对!第二天我刘世昌。好!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!“红尤二楼”,“红尤二楼”!瞧我一个人的。我一个人顶下来。
乙 一个人顶下来吗?
甲 哎,怎么顶不下来呀?
乙 红油二楼?
甲 哎!
乙 三楼就不油啦?三楼还油吗?
甲 我这……我干吗?我油三楼干吗?
乙 你不说是“红油二楼”吗?
甲 这是那戏!这是大楼,什么楼……那戏!
乙 那是《红楼梦》,尤三姐、尤二姐!
甲 我知道,你甭管,我就来这个。头天的《连环套》,我唱晚场戏,白天我不唱。
乙 白天不唱?
甲 晚场戏。早晨,八点来钟,客满!剧场,坐满啦!
乙 晚场戏,早应该坐满啦!
甲 不对号啊,不对号入座,谁不得早去呀?赴前排座儿,得听得看哪。
乙 对对。
甲 都早去呀。观众去得早,八点,满座!我还没起呢,我睡得着着的,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,扒开门一看:嚄!我心里话!
乙 哎哎!等等!八点应就满了,你怎么知道的?
甲 这,正把我吵醒啦。
乙 把你吵醒啦?你在哪儿睡觉啊?
甲 后台。
乙 哈哈,后台睡觉?你住旅馆、饭店哪?
甲 我不住饭店,我就住后台。我总住后台,我总跟箱官儿在一块儿睡。叠衣裳,叠行头那个箱官儿。
乙 你干吗跟他在一块儿睡觉?
甲 我就为盖他的被卧。
乙 嗬!这角儿!连被卧都没有。
甲 不是没有,不是没有!
乙 有?
甲 我有钱不置这东西,我嫌麻烦,出门打行李卷儿,带着麻烦。我有钱,我多置行头,门帘、大抬杠我有七十多个。
乙 七十多个?
甲 哎。
乙 你改俩被卧好不好?
甲 管得着吗?我乐意呀!我乐意呀。刚顶中午十二点多钟,又来四百多位,买票。前边不能卖票啦,座满啦!没票了。“没票啦?不行!我们也得听啊!我们听马喜藻马老板,
我们不是这此地的。我们打南京来的、苏州、杭州来的、蚌埠来的、徐州来的、有石家庄来的、有邢台来的。”你瞧,这么多人,怎么办?没地方坐啦!“买站票吧!”“站票?行!”“一万二!”
乙 啊?站票也一万二?
甲 照样一万二。四百多位,愣屈尊大驾站着听,太好啦!太捧马喜藻啦!太捧戏啦!站着听,四百多位。刚站好,又来了,又来三百多位,非听不可。剧场经理说:“这怎么办
呢?站票都满啦,您买蹲票行吗”?“我们乐意,乐意”!
乙 蹲着?怎么蹲?
甲 人都上边宽底下窄呀,两位的空档蹲一个,两位的空档蹲一个。
乙 好嘛!受罪来啦!
甲 哎,刚蹲好,又来一百七十多位!
乙 一百七十多位?
甲 这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,直掉眼泪。“我听不着马喜藻,简直活不了啊。”
乙 哎,至于吗?这个!
甲 哎呀,经理心软啦,说“这怎么办?买挂票吧。对!挂!好,挂吧!”
乙 挂?怎么个挂票?
甲 就一棵绳子拴一个,一棵绳子拴一个,往墙上,往墙上一挂。
乙 好嘛!受罪来啦?
甲 挂票!挂一百七十多位!
乙 好!
甲 嗬!我心里这痛快!扮戏呀,窦尔墩!刚要打花脸儿啊!
乙 哎!那叫勾脸儿。
甲 我说勾脸儿怕你不懂!勾脸儿……勾眼儿?
乙 勾脸儿!
甲 刚要勾脸儿啊,从后台进来一个人,大高个,戴着黑眼镜儿,茶镜、墨镜,咱说不清楚啊,大个!“哦,辛苦,辛苦,辛苦!众位!哪位马老板?哪位是马老板马洗藻?哪位洗藻?”
乙 好嘛,找洗澡的!
甲 “我,我!我,我姓马!”“哦,你好!实在该来啦!少拜望!不知你哪儿住!”
乙 噢?谁呀这是?
甲 不认得。“你干吗的?唱戏的?不认识啊,贵姓?”“金、金少山。”“少山?”
乙 金少山来拜望?好!
甲 “啊,您找我?有事儿吗?”“没别的事儿,听说您贴《连环套》,非唱《窦尔墩》哪?你要唱窦尔墩,我就没能耐,江南、华北一带,我小小有‘蔓儿’,都知道我唱的不错。今儿听您这个,再听我那个,我一分钱不值啦!无论如何,你赏我点饭吃,我来窦尔墩。”
乙 他要来窦尔墩。
甲 我说:“你来窦尔墩,我呢?”“您来天霸?”“谁?”“我少山来窦尔墩,你来天霸。”
乙 天霸,你也行?
甲 也行?把“也”字去啦!就是“行”!我说:“好!你扮吧!我给你画脸儿。”“哟!你甭管,我自己来。”我说:“你来,好!”他窦尔墩,我来天霸。我说:“谁?瑞安!瑞安!”
乙 瑞安是谁呀?
甲 周瑞安,周瑞安都扮好天霸啦!我说:“你算了吧!你改弃权,我天霸。”我扮好了天霸了。我扒台帘儿一看:少山这……这窦尔墩啊!
乙 那是真好!
甲 一文没有啊。
乙 啊?
甲 《盗马》的那个地方,咱一看,抬手动脚,跟我那个完全、一点也不一样。
乙 是啊!他要跟你一样?他也没被卧啦!
甲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。他唱的《坐寨》,那摇头、晃脑地一唱,谁给他叫好?打他一出场,那台下的观众就嘀咕:“嘿!好啊,好!马老板呢?马喜藻!”“金少山哟?”“马老板?一定‘天霸’。”都憋着给黄天霸叫好!
乙 听你的。
甲 听着咱这一上场,你琢磨琢磨这模样!扮出天霸来怎么样?
乙 猴儿啊?
甲 好,句句落好。他不落好,咱还不落好?他唱的没要下来。咱那天,我嗓子也不知怎么啦!
乙 是啊?
甲 那天我不知道那天我吃了什么啦?那天,嗬!我嗓子这个亮啊!(学唱)“一马离了……”哎?不对。
乙 不是这词儿。
甲 这是《汾河湾》啦!
乙 什么《汾河湾》?
甲 《武家坡》啦!我是“宝马?”我是“保镖……保镖……”什么?
乙 “保镖路过马兰关”。
甲 哎?那天你听啦?
乙 我没听!
甲 听啦!听啦。
乙 我没听。
甲 没听,你怎么把我词儿给记住啦?
乙 你的词儿?
甲 我就这词儿。
乙 谁唱都这词儿。
甲 我就这词儿。我就这词儿,“保……”
乙 保镖!
甲 哦,对!(学唱)“保镖路过马兰关哪,啊……!”一落腔,底下这观众,连楼上、带楼下,哗!
乙 你瞧这好啊?
甲 全走啦!
乙 那还不走?
甲 骂着街地退票。
乙 好啊!
甲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?活该你走!你不懂艺术。咱这玩意儿,货卖有识家。
乙 对。
甲 真有一百七十多位没走!
乙 爱听?
甲 墙上挂着,走不了啦!
乙 走不了啦?
马三立 王凤山演出本
卖挂票
台词:
甲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,这个台词,跟其它的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。相声它这里头啊,它也有文言、也有成语、也有谚语、也有俗语、也有小市民语气,有地方语,那是很多。
乙 哎。
甲 戏剧就不是啦。话剧呢,它就不能说大白话,大部分是文言。京戏啊?那京剧,它就得呀,它单有京剧的台词。它就跟咱们普通话一样啦。
乙 是啊?
甲 哎。别忙——它就不能说“别忙!”“且慢!”——戏剧的“且慢!”。
乙 哎。别忙。
甲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,平常谁这么说?你刚走那儿—— “且慢”。可舞台里头懂——你听着戏,他说:“且慢!”听戏就是“别忙”,让他“打住”。“罢了!”是“得啦!”一见面,请安,“参见老大人”、“参见父母”、“参见爹爹”——“摆了”。咱平常不用,“老没见,你好啊?我给你请安!”“哎,得啦,得啦!”不能“罢了”!用不上。这舞台上它有舞台词——“罢了”!“且慢”,“呜呼呀”!“呜呼呀”是纳闷儿,“呜呼呀”!不信?“你待怎讲?——你再说一遍——你待怎讲?”
乙 哎。
甲 “嘟!”是急啦。“嗯?”是不乐意了,不乐意啦——“嗯?”“嘟!”急啦!这场戏见官儿,给官儿跪下,最好是:“呜呼呀!”这犯人准有好处,带上堂来——“给大人叩头!”“抬起头来!”“小人有罪不敢抬头。”“恕你无罪。”“谢大人!”官儿一瞧:“呜呼呀!”行啦。
乙 怎么?
甲 呜呼呀!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。详细审问,好啦。“嘟!”——坏啦!
乙 怎么?
甲 倒霉啦!“给大人叩头。”“抬起头来!”“有罪不敢抬头。”“恕你无罪!”“谢大人!”“嘟!”倒霉,准糟!
乙 生气了。
甲 那可不!这戏剧很深,下功夫最难。“唱、打、做、念、翻”,这个……这个舞台上……
乙 哦,您对京戏很有研究?
甲 研究干吗?你不认识我?你不常听戏。
乙 那你?
甲 你常听戏吗?京戏,你听不听吧?
乙 我从小就爱听戏。
甲 你要常听戏,你不能不认识我。你不能不认识我!你认识我吗?
乙 不认识啊?
甲 你看看!你细看看,哎呀……你们爱好京戏,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我。
乙 是啊?
甲 你怎么不认识我呢?
乙 您是哪一位?
甲 杨……
乙 杨?
甲 杨宝森!
乙 杨宝森?你是杨宝森?
甲 真是不认识,拿我……拿我当杨宝森。我不是!我不姓杨。谁杨宝森?拿我当杨宝森!我不是杨宝森哪。
乙 您是谁?
甲 提杨宝森这个人,你知道不知道?
乙 知道。
甲 我给他蹬三轮儿。这多少年了吧。
乙 多少年了?哎,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儿啊!
甲 那玩艺儿!
乙 那玩艺儿也是蹬三轮儿啊。
甲 他蹬三轮儿,蹬我。
乙 哦,蹬你!拿你当三轮儿啦?
甲 拿你当三轮啦!我坐……我坐那儿,蹬三轮儿那蹬着,后来我让他,“你蹬宝森吧!”宝森净闹病,车是我的,我送给宝森。
乙 啊,送给他了。
甲 我不姓杨。
乙 哦!您是?
甲 马!北京你打听打听!北京你打听打听,唱戏的马老板!那谁不知道啊?
乙 哦,北京马老板?马连良?
甲 马连良干吗?马连良是我们本家,我们都一家子。
乙 哦,一家子。
甲 马连良是“连”字儿的。
乙 对。
甲 “富连成”,他排字排“连”字的!我们科班儿,那时候叫“喜连成”,听说过吗?
乙 听说过。
甲 “喜连成”!哎,我们“喜”字,雷喜福?知道吧?
乙 雷喜福,大师兄?
甲 哎,对。
乙 知道。
甲 我们一块儿的。这还用说吗?侯喜瑞知道吗?
乙 知道哇。
甲 侯喜瑞——“喜”字嘛,陈喜星、康喜寿、魏喜奎……没有魏喜奎,魏喜奎她改大鼓啦。
乙 没改!一起就唱大鼓的。
甲 不是魏喜奎,什么“喜奎”我忘了。
乙 哎,刘喜奎。
甲 刘喜奎,对。反正我们都“喜”字儿的。
乙 哦,您叫?
甲 喜藻。
乙 洗……我修脚。
甲 修脚干吗?
乙 你洗澡干吗?你那儿洗完啦,我这儿……。
甲 喜!排“喜”字儿那个“喜”呀。
乙 那个“喜”呀?
甲 不是洗澡的那个“洗”。道喜、福禄寿喜的“喜”。
乙 噢!澡?
甲 藻是那个……这个字还说不上来。
乙 他连名字都说不上来。
甲 草字头那个……我想想草字头那个。
乙 李盛藻的那个“藻”。
甲 哎,你要是不提,我还把他给忘啦!李盛藻,听过吗?
乙 听过。
甲 唱的怎么样?
乙 好啊。
甲 别捧,别捧!别捧,别捧!说实在的,李盛藻唱得行吗?
乙 不错。
甲 你认为怎么样?
乙 都认为不错。
甲 服吗?
乙 服!
甲 那就完了,那咱就没杠抬了。你服,就完啦。那我就……行啦。
乙 我服李盛藻,碍着你什么啦?
甲 你要服李盛藻就行啦,
乙 怎么啦?
甲 你认为盛藻好,那就成!我痛快。
乙 与你何干?
甲 他跟我学的。
乙 李盛藻跟你学的?
甲 有人听过吧?李盛藻唱的怎么样?他完全学我,也就是我教戏。我当初在科班时候,我给他排戏,那都是我教的,完全学我。
乙 是啊?
甲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的戏一样。李盛藻——我给起的名字,在科班他排字排“盛”字儿。我说他叫“盛藻”,你就知道跟我学的啦。
乙 怎么?
甲 我叫“洗澡”嘛,他叫“剩澡”——我洗剩下他再洗!
乙 好嘛!俩人一个盆儿。
甲 我总在江南,江南一带。上海到过吗?
乙 到过。
甲 南京呢?
乙 到过。
甲 到南方你打听打听,海外天子、独树一帜——马喜藻,我!嘿,镇江,你打听吧!镇江大舞台,那剧场为我盖的。
乙 是啊?
甲 苏州,我。
乙 哎哟!
甲 我……杭州。
乙 好。
甲 ……芜湖……我,我快啦,快啦!
乙 快“呜呼”啦!要死了这位!
甲 我说我要死啊?我说我要死啊?
乙 不你说你快“呜呼”了吗?
甲 我快到芜湖那地方去啦。
乙 哦,到那儿演出。
甲 我现在不演出,我这些年不唱啦,气的!我生气,不唱啦。
乙 跟谁呀?生这么大气?
甲 这话!在哪儿,在上海。这年头你看,一九……我想想啊,一九四五年,你看这多少年了吧?
乙 日本降服那年。
甲 哎,对啦,日本降服,一九四五年。
乙 跟谁呀?生这么大气?
甲 那时候,我在那儿教……教票友,现在不叫业余吗?那时候就是票友。
乙 对对。
甲 国剧社。我呀,我在那儿当教练,教练,我教练。
乙 教练?足球啊?是排球啊?
甲 足球干吗呀?我唱戏!足球干什么?
乙 不是教练吗?你也唱戏?
甲 不是教练……我……我叫指挥,不叫指挥,我把场子,服务员把着。
乙 什么呀?
甲 把场子。
乙 把场子也不对呀。
甲 我得听,我得排!
乙 那叫导演。
甲 对,对!导演。我给你导演。(冲乙捣眼)
乙 别!一会儿瞎啦,你给我捣眼?
甲 我去那儿当导演,我给排戏。
乙 噢。
甲 票友跟我学。哎,很多票友,大伙儿要求我:“马老板,跟您学差不离,几年啦!每月给您这么些钱,天天管您饭,请你舞台上,你给看看。没见过您走台,您演两场,看看您舞台身段儿,跟您学学。”
乙 哎,让你演演。
甲 很多票友,要跟着学,要看看舞台经验,看看咱舞台表演,怎么办?
乙 那……演吧。
甲 唱吧。
乙 哎。
甲 咱不为赚钱,就为了让票友学。
乙 对对。
甲 演两天儿。
乙 在哪儿?
甲 在黄金。
乙 黄金大戏院?
甲 啊,礼拜六、礼拜演两天。晚场戏,演两个晚场。白天我不唱。白天我睡觉,白天我歇着。演两天,票友们学,这不订好了吗?该着你生气。
乙 怎么生气啦?
甲 唉!那年啊,那年哪,那个谁呀?小云儿啊!他呀,这番儿……
乙 哎?小云儿是谁呀?
甲 尚。
乙 尚小云?那是尚老板!还小云儿呢?
甲 尚小云呢,他这番儿啊,到上海,黄金戏院——他唱啦!又改他唱啦!把我气的。我正走剧院门口儿,我一看:黄金大戏院门口贴着这么大的大宇:“尚小云。星期六开始演
出。”我一看,哎?咱定好啦——礼拜六、礼拜呀?
乙 就是啊。
甲 怎么改啦?我问问这个经理,怎么办?
乙 得问问。
甲 我进这剧场,我上楼,找经理。“我说经理呢?经理呢?”经理在屋里坐着呢,“啊,来,来!进来!正要找你,不知你哪儿住。”
乙 这角儿,没准地儿。
甲 “你呀!听信儿。啊,现在先别来。”我说:“咱不是订好了吗?礼拜六,礼拜。”“啊,尚老板来啦。”我说:“哪个尚老板?”“尚小云——尚老板。”“那么我呢?”“你听信儿。”
乙 听信儿?
甲 我说:“听多咱的信儿啊?”“听信儿!多咱剧场接不着角儿,你来。”
乙 好嘛,这位是打补丁的。
甲 把我气的!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?你就信他呀?我非唱不可,我就唱!
乙 你非唱不可,那不给人尚老板开搅了吗?
甲 我搅和他干吗?我非得黄金大戏院呀?
乙 哎……对。
甲 我这艺术,我就一家剧场学的?真是!天坛舞台。
乙 天坛大舞台?嚯?最大的。
甲 对啦!本来定两天,我改三天。
乙 比他多一天。
甲 咱赌这气儿,戗这火。多演一天,我演三天。
乙 演三天。
甲 瞧他票价卖多少钱?跟他比着。打听打听,黄金戏院,他这怎么样?票价?一打听,尚小云那儿——八千块!
乙 八千?
甲 前排每座八千块!一九四五年。
乙 可不多。
甲 贵啦!大发啦!大发啦,高啦!价码高啦!
乙 买个烧饼还一百块钱呢,尚老板卖八千块儿?
甲 不值,不值。
乙 太贱啦。
甲 这不天坛舞台跟我商量了,咱这票价怎么定啊?我说那边多少钱?他说“八千。”那儿八千,一想啊,我这儿啊……甭犹豫,干脆!
乙 两千块钱儿!两千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。不为听戏,为喝茶……对不?
甲 谁呀?谁呀?你说谁呀这是?谁呀?说谁哪?
乙 说你呀!
甲 八千,那儿八千。
乙 八干那是尚老板。
甲 我,我多少钱?
乙 两千块钱,不少啦!
甲 我不值钱,我不如他?在哪儿?哪儿?哪儿,哪儿?你看见啦?看见啦!你听说的?你看见啦?你是听说啦?你看见啦?你听人说的还是你看见啦?
乙 我这么琢磨着。
甲 呸!要不这种人!你就不能搭理他,你不能理他呢!这儿还慢慢告诉你:八千、八千!他那儿八千!我两千?还带点儿好茶叶、管饭。我跟你要价,我算栽啦,我算栽跟头啦!
乙 哦?那您卖多少?
甲 卖多少钱呢?一万二!
乙 啊?前排一万二?
甲 前排干吗?不管前排,什么前排后排,一律一万二。前后排不对号。
乙 一万二?
甲 不对号入座,你赶上前排一万二,后排一万二。楼上、紧后边,照样一万二。
乙 嗬!这价码可高。
甲 就这价。听戏的,观众不在乎钱,看的是玩艺儿,听的是戏,咱三天戏码得硬。
乙 哎,头天是什么戏?
甲 啊?头天呢,《连环套》。
乙 《连环套》?
甲 “盗钩”。
乙 嘿!这戏好戏。
甲 嘿!《坐寨》、《盗马》、《拜山》、《盗钩》唱全啦!窦尔墩、尚小云来一个?尚小云来窦尔墩?
乙 来不了,来不了!
甲 噢,噢!完了吧!
乙 第二天呢?
甲 第二天呢,第二天我来一个《奇冤报》、《乌盆儿记》。
乙 老生戏?
甲 唱功戏。
乙 老生你也成啊?
甲 也行啊?也行啊!唱、打、做、念、翻,全活儿!
乙 老生,你去谁?
甲 《奇冤报》——老生!头天,我“窦尔墩”!《连环套》。
乙 别说窦尔墩!这《奇冤报》老生是谁啊?
甲 我唱功戏呀。
乙 是啊?去谁呀?
甲 第三天呢,我一想啊,我来一个……
乙 别,别三天!第二天。老生是谁?
甲 我知道。第二天啊,第二天啊,老生啊,谁呢?《乌盆记》嘛,他那个谁?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,做成盆儿嘛。
乙 对对,他叫什么名字?
甲 你瞧,(唱)有那公俺做了……
乙 行行。
甲 别忙,一会儿,这词儿就出来了。
乙 准问词儿啊?问你叫什么名字?叫什么?
甲 徐世昌。
乙 什么?
甲 徐世昌。
乙 徐世昌?刘世昌!
甲 对!刘世昌,刘世昌!对!我说成徐世昌了。刘世昌!
乙 徐世昌?那是大总统!
甲 刘世昌,对对!第二天我刘世昌。好!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!“红尤二楼”,“红尤二楼”!瞧我一个人的。我一个人顶下来。
乙 一个人顶下来吗?
甲 哎,怎么顶不下来呀?
乙 红油二楼?
甲 哎!
乙 三楼就不油啦?三楼还油吗?
甲 我这……我干吗?我油三楼干吗?
乙 你不说是“红油二楼”吗?
甲 这是那戏!这是大楼,什么楼……那戏!
乙 那是《红楼梦》,尤三姐、尤二姐!
甲 我知道,你甭管,我就来这个。头天的《连环套》,我唱晚场戏,白天我不唱。
乙 白天不唱?
甲 晚场戏。早晨,八点来钟,客满!剧场,坐满啦!
乙 晚场戏,早应该坐满啦!
甲 不对号啊,不对号入座,谁不得早去呀?赴前排座儿,得听得看哪。
乙 对对。
甲 都早去呀。观众去得早,八点,满座!我还没起呢,我睡得着着的,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,扒开门一看:嚄!我心里话!
乙 哎哎!等等!八点应就满了,你怎么知道的?
甲 这,正把我吵醒啦。
乙 把你吵醒啦?你在哪儿睡觉啊?
甲 后台。
乙 哈哈,后台睡觉?你住旅馆、饭店哪?
甲 我不住饭店,我就住后台。我总住后台,我总跟箱官儿在一块儿睡。叠衣裳,叠行头那个箱官儿。
乙 你干吗跟他在一块儿睡觉?
甲 我就为盖他的被卧。
乙 嗬!这角儿!连被卧都没有。
甲 不是没有,不是没有!
乙 有?
甲 我有钱不置这东西,我嫌麻烦,出门打行李卷儿,带着麻烦。我有钱,我多置行头,门帘、大抬杠我有七十多个。
乙 七十多个?
甲 哎。
乙 你改俩被卧好不好?
甲 管得着吗?我乐意呀!我乐意呀。刚顶中午十二点多钟,又来四百多位,买票。前边不能卖票啦,座满啦!没票了。“没票啦?不行!我们也得听啊!我们听马喜藻马老板,
我们不是这此地的。我们打南京来的、苏州、杭州来的、蚌埠来的、徐州来的、有石家庄来的、有邢台来的。”你瞧,这么多人,怎么办?没地方坐啦!“买站票吧!”“站票?行!”“一万二!”
乙 啊?站票也一万二?
甲 照样一万二。四百多位,愣屈尊大驾站着听,太好啦!太捧马喜藻啦!太捧戏啦!站着听,四百多位。刚站好,又来了,又来三百多位,非听不可。剧场经理说:“这怎么办
呢?站票都满啦,您买蹲票行吗”?“我们乐意,乐意”!
乙 蹲着?怎么蹲?
甲 人都上边宽底下窄呀,两位的空档蹲一个,两位的空档蹲一个。
乙 好嘛!受罪来啦!
甲 哎,刚蹲好,又来一百七十多位!
乙 一百七十多位?
甲 这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,直掉眼泪。“我听不着马喜藻,简直活不了啊。”
乙 哎,至于吗?这个!
甲 哎呀,经理心软啦,说“这怎么办?买挂票吧。对!挂!好,挂吧!”
乙 挂?怎么个挂票?
甲 就一棵绳子拴一个,一棵绳子拴一个,往墙上,往墙上一挂。
乙 好嘛!受罪来啦?
甲 挂票!挂一百七十多位!
乙 好!
甲 嗬!我心里这痛快!扮戏呀,窦尔墩!刚要打花脸儿啊!
乙 哎!那叫勾脸儿。
甲 我说勾脸儿怕你不懂!勾脸儿……勾眼儿?
乙 勾脸儿!
甲 刚要勾脸儿啊,从后台进来一个人,大高个,戴着黑眼镜儿,茶镜、墨镜,咱说不清楚啊,大个!“哦,辛苦,辛苦,辛苦!众位!哪位马老板?哪位是马老板马洗藻?哪位洗藻?”
乙 好嘛,找洗澡的!
甲 “我,我!我,我姓马!”“哦,你好!实在该来啦!少拜望!不知你哪儿住!”
乙 噢?谁呀这是?
甲 不认得。“你干吗的?唱戏的?不认识啊,贵姓?”“金、金少山。”“少山?”
乙 金少山来拜望?好!
甲 “啊,您找我?有事儿吗?”“没别的事儿,听说您贴《连环套》,非唱《窦尔墩》哪?你要唱窦尔墩,我就没饭啦!虽然说我没能耐,江南、华北一带,我小小有‘蔓儿’,都知道我唱的不错。今儿听您这个,再听我那个,我一分钱不值啦!无论如何,你赏我点饭吃,我来窦尔墩。”
乙 他要来窦尔墩。
甲 我说:“你来窦尔墩,我呢?”“您来天霸?”“谁?”“我少山来窦尔墩,你来天霸。”
乙 天霸,你也行?
甲 也行?把“也”字去啦!就是“行”!我说:“好!你扮吧!我给你画脸儿。”“哟!你甭管,我自己来。”我说:“你来,好!”他窦尔墩,我来天霸。我说:“谁?瑞安!瑞安!”
乙 瑞安是谁呀?
甲 周瑞安,周瑞安都扮好天霸啦!我说:“你算了吧!你改弃权,我天霸。”我扮好了天霸了。我扒台帘儿一看:少山这……这窦尔墩啊!
乙 那是真好!
甲 一文没有啊。
乙 啊?
甲 《盗马》的那个地方,咱一看,抬手动脚,跟我那个完全、一点也不一样。
乙 是啊!他要跟你一样?他也没被卧啦!
甲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。他唱的《坐寨》,那摇头、晃脑地一唱,谁给他叫好?打他一出场,那台下的观众就嘀咕:“嘿!好啊,好!马老板呢?马喜藻!”“金少山哟?”“马老板?一定‘天霸’。”都憋着给黄天霸叫好!
乙 听你的。
甲 听着咱这一上场,你琢磨琢磨这模样!扮出天霸来怎么样?
乙 猴儿啊?
甲 好,句句落好。他不落好,咱还不落好?他唱的没要下来。咱那天,我嗓子也不知怎么啦!
乙 是啊?
甲 那天我不知道那天我吃了什么啦?那天,嗬!我嗓子这个亮啊!(学唱)“一马离了……”哎?不对。
乙 不是这词儿。
甲 这是《汾河湾》啦!
乙 什么《汾河湾》?
甲 《武家坡》啦!我是“宝马?”我是“保镖……保镖……”什么?
乙 “保镖路过马兰关”。
甲 哎?那天你听啦?
乙 我没听!
甲 听啦!听啦。
乙 我没听。
甲 没听,你怎么把我词儿给记住啦?
乙 你的词儿?
甲 我就这词儿。
乙 谁唱都这词儿。
甲 我就这词儿。我就这词儿,“保……”
乙 保镖!
甲 哦,对!(学唱)“保镖路过马兰关哪,啊……!”一落腔,底下这观众,连楼上、带楼下,哗!
乙 你瞧这好啊?
甲 全走啦!
乙 那还不走?
甲 骂着街地退票。
乙 好啊!
甲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?活该你走!你不懂艺术。咱这玩意儿,货卖有识家。
乙 对。
甲 真有一百七十多位没走!
乙 爱听?
甲 墙上挂着,走不了啦!
乙 走不了啦?
马三立 王凤山演出本
打电话,13课
~
#韦婕肺# 求小学生(五年级)3 - 4人搞笑小品,要短的! -
(17358519549): 草船借箭缩写400字(七) 草船借箭缩写 周瑜很妒忌诸葛亮(字孔明)的才干.因水中交战需要箭,周瑜要诸葛亮在十天内负责赶造十万支箭,哪知诸葛亮只要三天,还愿立下军令状,完不成任务甘受处罚.周瑜想,三天不可能造出十万支箭,...
#韦婕肺# 跪求小学五年级的5人搞笑小品,,快到元旦了快点谢谢 -
(17358519549): 《新笑林》
#韦婕肺# 有没有适合小学生演的爆笑小品?急!急!!急!!! -
(17358519549): 搞笑课本剧《乌鸦与狐狸 角色:乌鸦甲,乌鸦乙,(文中以甲乙代替),狐狸. 旁白:这是一个发生在猪肉价格猛涨时期的真实故事,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森林里,乌鸦小姐收到了好心人寄来的两斤猪肉~~~~~ (舞台灯光溅亮,甲乙惊喜的蹲着...
#韦婕肺# 小学生四人表演的爆笑小品 -
(17358519549): 偷车情缘(校园小品) 人物:男偷T,女偷T,男生S,女生S 场景:长椅边 内容:男偷背包上:天气好,抖精神,拿上家伙跨出门,不靠家,不求人,富裕全都靠个人! 你问我是做什么?嘿嘿!(拿出背包里的一大串钥匙)偷车神! 女T上:...
#韦婕肺# 有没有什么搞笑的小品,适合小学生的小品,而且要5个人的. -
(17358519549): 清早去买鱼,不料因为价格和老板打起来了.混战之中,他抓起冻鱼对着我就是一顿狂打,我瞬间就被打蒙,那一刻,什么都不知道了,只感觉冷冷的冰鱼在脸上胡乱地拍...
#韦婕肺# 五年级适合演的相声、、小品 -
(17358519549): 发了一个相声《你爷爷我爷爷》,希望有用. 你爷爷 我爷爷甲:问你个事?乙:什么事啊?甲:你认识我爷爷吗?乙:噢!你爷爷啊!甲:熟悉吧?乙:不认识!甲:....我认识.乙:唉呀,真了不起啊,你连你爷爷都认识.甲:要不人家说我智...
#韦婕肺# 小学生5人小品剧本,要搞笑的,爆笑最好,注意(五人)小品.... 六一马上要到了,我们小学生要表演小品.急 -
(17358519549): 我觉得5个人可以演啦啦啦德玛西亚第一集,正好5个人,而且好玩,也可以出一些有创意的.爆笑校园和阿衰上的一些好玩的行为或语音可以融入.
#韦婕肺# 小学生演的小品搞笑 -
(17358519549): 人物:王婆甲、乙、丙;顾客子、丑、寅. 地点:吹街炒市. 时间:离永远没多远. 王婆甲:快来买,玉女牌西瓜,保甜保熟保沙瓤哩! 顾客子(举瓜敲了敲):你这瓜不熟吧? 王婆甲:熟大发就娄了.再者说,熟的档期已满,你请得动吗?...